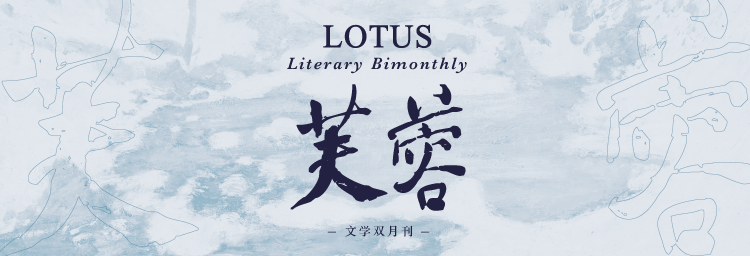

晴空一鹤
文/刘静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注定是中唐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里,大明宫换了三位皇帝,德宗、顺宗、宪宗,第二年正月十九日,宫里忽然传出太上皇李诵暴毙的消息,终年四十六岁,死因成为历史疑案,而这一切都与那场历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有关。唐宪宗即位后,王叔文首当其冲被贬为渝州司户,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革新派的其他成员也如同惊弓之鸟等待厄运的降临,这就是“二王八司马”事件。
一个月后,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位权力核心的政要均被贬为“州司马”,在萧瑟的秋风中踏上了万死投荒的远贬之路。然而,与柳宗元的凄苦和孤独不同,刘禹锡对贬谪生活的适应能力似乎超出常人,尽管有“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的感慨,但弃置之路并没有使他的意志消沉,反而更加磨练了这个昂扬倔强的生命。
一
秋风萧瑟的九月,时年三十七岁、本为“金闺玉堂”的屯田员外郎刘禹锡被“投置闲散”——新帝下诏,贬为连州刺史。
途中一日,天蒙蒙亮,一夜无眠的刘禹锡披衣信步外出,破晓时,笼罩人间的黑暗虽迟迟不肯退去,东边的天空却已经被尚未升起的太阳照亮,赤艳的朝霞更是倔强地映红了波涛滚滚的长江。刘禹锡极目远眺,若有所思亦若有所悟,恍惚间,他仿佛看到一戴着斗笠的高人,向着远处渐行渐远,皎洁灵秀,空明澄澈,潇洒自在,不染俗尘;耳旁亦似乎传来了儿时熟悉的寺庙禅音——“师傅”!此时,幼时在双亲的守护与陪伴下与病魔斗争的点点滴滴亦顷刻间涌上心头,刘禹锡沉浸在回忆里,他看到了时间,也看到了自己——因多病的身体,反而磨炼出倔强与不屈的孩童。他心中那股郁结之气此刻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猛然上蹿,伴随着这长江之上的苍茫之气,终化作一声声怒吼喷涌而出,“哈哈哈哈!”刘禹锡大笑于江边,于这天地之间。
随后,他利落地转身,再次登上了南下的船,傲立于船头,一路吟唱:“ 轻阴迎晓日,霞霁秋江明。草树含远思,襟怀有余清……渚鸿未矫翼,而我已遐征。因思市朝人,方听晨鸡鸣。昏昏恋衾枕,安见元气英。纳爽耳目变,玩奇筋骨轻。沧州有奇趣,浩荡吾将行。”(《秋江早发》节选)
同年十一月,就在刘禹锡赶赴连州的路上,朝议谓王叔文之党贬之太轻,新帝追发敕命,再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朗州就是如今的湖南常德,在唐朝的时候,人烟稀少,地方偏僻,经济不发达,被描绘为遍布丛林、沼泽、瘟疫、毒草、野兽的危险之地。
敕命传来,刘禹锡正在岳阳与前来为他接风的友人于酒肆中畅谈,得知这一消息,刘禹锡反倒欢笑,“如此甚好!朗州不过在长沙之下,省却了许多路途颠簸,甚好!刺史劳碌不堪,司马清闲有加,甚好甚好!”于是推杯换盏之后,满席又是欢声笑语,一夜畅饮。
翌日清晨,刘禹锡习惯性早起,留诗,以代话别,“马踏尘上霜,月明江头路。行人朝气锐,宿鸟相辞去。流水隔远村,缦山多红树。悠悠关塞内,往来无闲步。”(《途中早发》)
无论遭受怎样沉重的打击,刘禹锡始终凭借超凡的豁达胸襟和顽强意志,将这些逆境视为锤炼自我、磨砺品质的机会,每一次挫折,都似乎在他这里转化为了一种向上的动力,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出更为磅礴的力量。
朗州近在咫尺。
(节选自2024年第5期《芙蓉》刘静的散文《晴空一鹤》)

刘静,男,1973年出生,湖南华容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湖南某省直单位。在《芙蓉》《湖南日报》《新湘评论》等报刊发表多篇作品。
来源:《芙蓉》
作者:刘静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