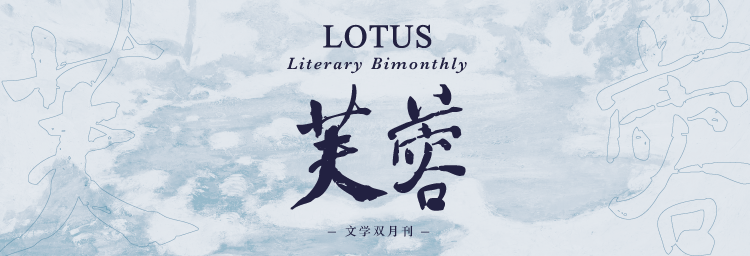

熬粥(中篇小说)
文/王哲珠
勺子搅着粥,米粒轻轻腾跳,离开谷穗之后,它们在此刻重新获得了生命力,像曾经吸收阳光,吸收着排骨的精髓和火的能量。何树成舀起半勺米粒,细细凝看,说:“排骨和米一块下锅,肉香和米香要慢慢熬出来。一定得用砂锅,米粒在砂锅里会喘气,砂锅能把每粒米都照顾得好好的。现在的人老用高压锅压,那叫什么粥,把骨肉和米都压死了,没有用心思熬什么粥。”每次熬粥,只要何铭在,何树成总要重复这些,虽然何铭一再声明,他以后不会走熬粥这条路子的。
“春菜切细一些,菜茎先煮,菜叶缓一点下锅。”何树成不管何铭的态度,继续讲,他更像是自说自话。何铭知道,父亲沉进粥的世界里了。他拿好了碗筷,自己倒了小碟酱油,等着父亲把那锅粥端上桌,这是属于他们父子的时间。晚上,送走最后一个客人,关了店门,何树成总熬一锅粥,两人慢慢喝。何铭上大学后,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
端起碗,何铭突然抬起脸,问:“爸,我是你亲儿子吗?”
那一瞬,何树成表情凝固,猛地咬紧齿间一块排骨,手却一松,手里那碗粥滑脱下去。碗的碎裂声在何铭脑子里炸开,他身子一跳,惊醒过来,人跌在沙发脚。
只是梦,何铭又庆幸又懊恼。现实中,这句话还没法出口,一旦出口,这句话将像锋刃,把他平滑正常的生活割开一个口子,口子里有什么,他无法想象也不敢想象。虽然之前的日子也不算世俗中的正常,但他已经适应,认定成自己的生活。在此之前,他一直错觉那样的日子会地老天荒的。可那句话不出口,日子就能这么“正常”下去吗?何铭发现,话出不出口,那道口子都在了,那个疑惑纠成死硬的结,哽在胸口,每次呼吸他都感觉得到。他抱住头,身体蜷成一团,好像这样就能避开什么。事实上,自他听见大姨冯秋芬和父亲那番话后,他就再也避不开了。
大姨冯秋芬回来了,开始,何铭以为是因为外公冯奕东的身体,后来才发现有更重要的原因。自何铭记事起,外公冯奕东的身体就不太好,大部分时间是在轮椅上度过的,但脑子一直很清醒,近期却糊涂起来,去了医院,被诊断为老年痴呆。冯秋芬回娘家也就看看老人,跟老人聊一聊,把老人当小孩哄一哄,照顾老人的还是何树成,这已经成为他日子的一部分。
“你弄这个做什么。”冯秋芬冲何树成晃着几页纸,“爸清醒的时候立的?要不是你的意思,爸会弄这个?懂得弄这个?你什么意思?何铭才二十岁,你几岁,你现在安排这个?”
何铭知道,那几页纸是冯奕东立的遗嘱,父亲给他看过。那时冯奕东脑子清晰,何树成请了律师做见证的,这份遗嘱是有效的,遗嘱清清楚楚地把何铭定为“冯氏粥店”的继承人。对“冯氏粥店”,冯秋芬说她没有半点兴趣,她远嫁他城,生活无忧,这点冯奕东很清楚,她也不止一次对何树成表明过。冯秋芬对何树成说:“我自己是不要,可我不是这个意思。”
何树成不出声,现在冯奕东没法讲事情了,这事不跟冯秋芬打招呼是冯奕东的意思,冯奕东讲得很明白:“秋芬不稀罕这粥店,这是我的事,跟她有什么好说的。”可这话只有何树成听到。发现自己越来越容易忘事,冯奕东就有不祥的预感了,他先跟何树成提到“冯氏粥店”,他原先的意思不是遗嘱里那样的,是何树成说服了他。
沉默了一会,冯秋芬说:“阿铭毕竟不是……”
何树成猛地止住了她。
“这事没的改了吗?我回来就是问问这个。”冯秋芬说。
那时,何树成和冯秋芬在二楼,何铭立在楼梯上,走了一半的他不知是否该继续上楼。最终,他下了楼,转身出门,在外面逛了一圈。很明显,大姨冯秋芬不愿让他继承“冯氏粥店”,他在意的不是这个,他只是疑惑,大姨自己不要粥店,外婆去世了,除了他这个外孙,冯家没什么直系亲属了,大姨想把粥店留给谁?给父亲?当然,给父亲是最合适的最好的,跟给他是一样的,他只是疑惑……还有大姨那句讲了一半的话。
那一瞬间,之前那些疑惑全涌出来了,也是那一瞬间,何铭才发现,那些疑惑不是从今晚这件事才开始的,不知从哪一天起,已经悄然积聚着,只是被他的下意识按压在某个角落。
很小的时候,邻居的小孩就嘲笑过何铭,说他是捡来的孩子,或说是被扔掉的,甚至有说是被偷来的。这些话的根源是当时大人们窃窃的闲话,落入一些顽皮孩子的耳朵,明里暗里地传来传去。何铭和玩伴打架,回家向何树成哭诉。何树成给他的理由是:“你妈妈去世了,我们的日子跟他们有点不一样,他们就乱猜,别理他们。”
他们乱猜的。何铭将父亲的解释当作支撑点,可还是有疑惑。关于母亲,父亲极少提,能不提就不提。对何铭的追问,或回避或敷衍。在何铭的记忆里,他差点拥有一个新的母亲。
那个女人在店里做了大半年帮工,大人们都觉得跟父亲挺合适的,用外公的话说,看着是个过日子的人,一次闪劝父亲和那个女人搭伙。那女人对何铭不算多好,但该有的照顾和礼节,她做得挺周全的。那年,何铭十二岁,懂得表示他的态度了,不赞成也不怎么反对,一切顺其自然的样子。那女人最终没有走进父亲的日子,何铭不知道其中缘由,也从未问起,但他一直记得她和父亲争吵过,因为什么吵,记忆挺模糊了,那女人一句话却极清晰,她说:“为一个不相干的孩子,这样……”那时,何铭认为她说的不相干是自己与她。在后来的岁月中,他慢慢意识到,那个不相干指的是他与父亲,这个意识隐得那么深,以至他从未发现,或许是不愿承认。这时,当年这句话突然清晰起来。
梦里的那句话要不要问出口,怎么问出口?胸口那个结愈来愈坚硬,从白天的日子纠缠到夜晚的睡梦里。某个晚上,再次从睡梦中醒来时,何铭脑子闪出这几个字:亲子鉴定。这几个字变成更大的结,搅得他不得安生,他问自己,真不要日子了吗?他头皮发麻,额角发痛,他只想跟父亲静静喝粥。
(节选自2024年第5期《芙蓉》王哲珠的中篇小说《熬粥》)

王哲珠,广东揭阳人,80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各文学杂志发表小说两百多万字,有小说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选刊转载。出版长篇小说《老寨》《长河》《琉璃夏》《尘埃闪烁》《我的月亮》《姐姐的流年》,中篇小说集《琴声落地》《什么都没发生》。
来源:《芙蓉》
作者:王哲珠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