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度理性铺陈下的现代主义审美
——余怒诗歌论
文/陈啊妮
余怒的诗歌实践,极好地处理了语言的相对性和永在性的问题。他的诗歌,立足于当代,却能在未来继续与时俱进般地生长。正因此,读者往往不能轻易进入他的“诗境”,诗人并不对读者的阅读乐趣刻意逢迎,而是我行我素,这种只对文本负责,或对未来负责的态度,实则是高明的。韩东曾这样评价余怒:“这是一个将诗歌作为精神容器的诗人,也基本做到了人思一体,殊为难得”。我很赞同韩东的观点。余怒所拥有的,是个经他“精神变构”的特殊的宇宙,这与诗人内心的空阔是相伴相生的,而他每一首诗的出发点,又是平凡生活中,某一刻的极普通的细节或小事物,以小搏大,以实至虚,是高度理性铺陈下的现代主义审美。余怒诗歌聚焦于自身的生活,或生活中的小环境与小气候。窗外楼下所发生的一切,也可能不是他所关心的,除非它们通过某种方式传递到他的身边。余怒说过:“个体的感受才是真正诗性的东西”,而个体感受既有感官的,也是心理上的;既有被动击打的,也有主动触抚的。总之,他的诗成于真实而真切的接触、互观与碰撞。如在余怒诗中,纯粹属于天真烂漫状的想象力的东西,是少之又少的,或没有。他的超验体验,得益于词与句没道理的“偶遇”,一刹那间的个人惊醒,却被他捕获锤炼成特别意味来。通过阅读他大量的诗章后,会发现绝没有固定的叙述方式,在诗歌上的变化也丝毫不顾忌别人对他的再认识的难度,以及不同的评价。他坚信变化才会有一切,变化才能够保持诗歌的呼吸。变化才能让他的诗歌有生命,他本人才能够在一首诗歌里面活着。
所以,对于余怒的诗歌,使用“辨识度”这个词显然有点荒唐。他的诗歌的变化不仅仅是诗歌叙述形式上的变化,而是用词汇、语言,对事物的阐释,逻辑关系,以及思维方式的变化。同样一个事物,可以被他命名多次。通过不断地命名,加深对于特定事物的再认识。余怒诗歌所体现的,确实如他所说的,是在竭力寻找和建立与某物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个体的,当然也是诗性的、直截了当但很容易忽视或放手的,一种只能通过诗歌基本说清的感觉。余怒对“关系”的建立到了痴迷之境,诗人不就是拿关系说事的吗?也许关系本身,就是诗性发现;这种关系越奇特,越不可思议以至妙不可言,就越有把这一关系记录下来的必要。比如《有所获》中,一个奇怪的问题从天而降:“清晨我写下第一个句子/来到户外/我在考虑,什么是/‘巨大的东西’,尤其是/那‘巨大’为何物所容”,在此感觉的衍生物便是这“一问”,诗中所罗列的“一座桥”“一树柿子”“大气层”,都是巨大的东西吗?我们只能说,这些事物此刻对诗人产生了巨大的“意象”或“意味”,读者可以沿着他的思维前进,也可能因“不屑”而停下来,或某个时间的当口,忽然又想到这几个句子,被“他的巨大”所降服,或吞噬。诗人在《万物和你》中,已把他与“万物”间的关系说得很明确了:“万物存于我心/是影子,不是万物/你存在,不是物理存在/不是我们所见的/这一个或那一个不是万物,在这般/显现之后以其光存于我心。”万物是个复杂的存在,尤其是它的内在,也包括它外在浅表细微的迁移和风化,诗人所能感触并能把握的,只是表面的光,和它的身体的影子,“光与影”就是诗人与事物的关系,很纯粹。
余怒的诗作酝酿过程一定是孤独的,是孤独中的左冲右突,或远近徘徊。他并不着急于打开缺口突围,而是笃守于一隅做足功夫,通过细微而逼仄空间的“发酵”,“膨化”出诗意。我想,这一切仰仗于宁静的孤独,静到极致也孤独到极致才能产生的体验。如《独处篇》中:“斑叶栀子花的纯白花瓣散发的/浓郁芬芳在卧室里萦回,多次令我不安。”花香令人不安,我想需要多维度的感应才能产生,是诗人从芳香中,闻及超过气味品质的另一种力量,让他呼吸异常。诗中后来写到他和这个世界的“依赖”关系,则是此诗的一个核心。是花香的弥漫令诗人想起周身与外界的连接,牵绊或摩擦,意料中的或不可测的,当邻居女人敲门借物时,我们才明白:一切关系的产生寓于必然,同时必须又出乎于偶然。不是吗?“美是绝对的”——这句话道尽了所有的机会的把握或丧失,欢欣或悲苦,皆能产生美,如桅子花香弥漫于空气,怎么说都是一种美。这样的花的香味,我们是无法拒绝的,无论是在节日广场或葬礼上。《旅行札记》就是诗人在“小旅店”完完全全对室外声响的感受,用的是听力、视力和想象力,但主要是听力。如果诗人因好奇而身去看个究竟,就没有这首诗了。所以,个体感受的角度和深度,是能否产生“诗性”很重要的方面,保持一种“悬置”和“游离”,一种不确定和模糊,就是保证叙述的空间。诗中所见到的“鳞翅目昆虫”和“月亮”,是视力,但“被吹过幽暗乔木林的风所改变”和“像某个几何体,或空虚泛蓝的永恒”,则是内心的观照。同时,诗歌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瞬间的感觉。这种感觉只能用诗歌来表达,别的话说不出来,也不完整,更不准确。另外瞬间的感觉是最准确的,往往是真理在那一瞬间显露面目。《物恋篇》这首诗,是诗人总结性或概括性的写“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物是日常物,也是人一天中与之关联度最大的物品,也是一日生活最大的依赖,是扎扎实实、芜杂又易“致幻”的生活资料:“我有一块抹布擦拭每一件家具/我有一个计时器警告每一桩事情”,这是诗人的平凡生活、也是诗性生活的一部分。余怒力图通过物象之间,或人与物象之间的关系,来更好凸显人的生存况境,如同通过对一个人影子的观察,来断定他正往下俯身,当然也只有处于静寂中,才能唤醒我们对关系的投射与关注。其实,余怒的这一审美取向,也反映了他对“物相”或“物质”的质疑和认定,而更关注于精神和意识(无法量定的非物质),如《物与诗》中:“世俗的欢愉,人间的美景,这一物/与那一物,不过是这一首诗与那一首诗”,只要人与万物间的关系存在,就会有诗歌替代万物。余怒甚至把那些无法进行物理触抚的事物称为“感性事物”,这应是诗人专有物质,如“一个男人,被他的狗拖拽着/围绕我转一圈之后离去/这行为,也充满感性”(《感性事物》),我们不可排斥它的存在,但又很难用言语精确表达它,它就是一种“关系”,或感觉。
诗人不乏智性或哲思光辉的闪烁,具体表达上,又没有摆出哲人的姿态,而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说的日常用语,其智性和哲思是不经意中横溢出来的,也许这种了无痕迹本身也是智性本身。如《雪中拼图》中,诗人对“雪”的认识,或对青春和美的认识,也是一刹那间产生的一个亘古不变的法则:“任何/飘荡的东西任何凝固/的东西任何始与终的循环”,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诗中其他句子,来领略一种意味,如“堆雪人雪狮子雪城堡来表达一个/成年人对世界的全部期待蛮/可笑的”,诗人揭示的是流动的或加速衰败的美和洁白,无论用雪能堆成人或狮子,但这首诗又表达了一种“不变”,如“纯净本身和大理石”,世界也是由瞬间组成的,由系列变化聚合而成的不变。又如《汹涌之物》这首诗,一些“美妙的想法”,也是奇特或破天荒的怪想法,如果真的去试行了,会怎样?这首诗中,写了一系列新奇想法,且不论如何去实现,通过这些想法,我们会有个结论:不可能,但想想挺好玩的。比如:“把岸上日积月累/的所有汹涌之物一股脑儿/推入大海。你瞧瞧那波涛”,世界会乱吗?或这个世界依然会煞有其事地运行,并且产生了新元素,建立了新的冲突与平衡,人与人之间新型的挤兑、互踩或互助关系将大行其道。在此,诗人类似于打开新的一扇窗,意识的,也是哲学的,也是依靠诗人凭空“感觉”“臆造”出另一群人类和灵性时空,实则是诗人打开了更辽阔的自己——世界我们无能为力,唯有自我心灵深处的掘进。又如《关于痛苦》中:“而哲学意义上的痛苦也将成为诗/就像在诡异奇幻的冒险乐园里,危险是/孩子们的快乐之源,由成年人设计”,对“危险”的刺激的享受,是儿童的专利,又何尝不是成年人自身的?就像诗人在另一首诗《这很微妙》中写的:“被身体否定,这很微妙/仿佛一次化妆旅行/出一身汗之后/的一激灵顿悟”,从这几首诗中,我可以领略到诗人对生活中稍纵即逝的特殊“关系”的成立和特别感触的获取,是多么精心。
《露脊鲸和军舰鸟》是余怒的一首名作。大海给予人类的,除了生命之源,应该还有无尽的秘密。对大海的认识会是无止境的。诗人和大海的关系,是缓缓建立,又是突然成形的。在大海面前,人总会豁然有种自由的感觉,这是大海的赠予,然后是大海无形但有力的诱惑,让你成为海的部分。面对大海,如站在神灵脚下,情不自禁就会有祈愿之欲。大海是无所谓生与死的,它就是永生,也是恒定的死亡;它是出发,也是归宿;它是源头,也是终结;它是最大的大,也是最小的小。因而,我们在这一首诗里,读到了由客观至虚茫,由“我”的体感和心动,到“我”的变形,直至精神状态的“变通”:“想象今天我是一头露脊鲸/明天我是一群军舰鸟/或作为它们分别去体验”,由水里的巨无霸,变回浪头上子弹大小的微鸟,大与小的回转,及鱼与鸟的生命载体,在我来看,都属于海,是海的衍生物或是海的身体的不同展示。在此,我们还是要回到诗人与大海间建立的关系,由简单的人与物的观望,转入灵魂冥冥中的抚慰,世间的人与事,皆在此化整为零。诗人因为“寄生”于“露脊鲸”与“军舰鸟”从凡人与大海的关系中成功跳脱:“晨光中,军舰鸟因翅膀触水而惊起/露脊鲸因被浪花溅了一身而变蓝”,“我”仍是独立的,仍是一个肉眼可辨的存在,怎能不说是诗人的胜利呢?平心而论,余怒的诗不可解读,但解读余怒对个别性阅读者又是有趣也是有意义的,虽然不可能完全抵达诗人当时写作时的心境和感受(相信诗人本人也不能完全说得清那一刻了),但我依然作了尝试。
余怒也写过长诗的,但他的近作(如新诗集《蜗牛》中的100多首诗)以不超过十行的短制为主。诗的长短或用字的多少,并不等同于诗歌的容量,这在诗界已是共识,而对于余怒,就更为如此。文字显得简短,当然更不代表阅读难度的降低,或故作玄虚力度的增强。目前余怒诗歌的定位,是将对事物“物态”的描述用最“天真”“纯朴”的话语说出。这些话语,是不加任何修饰性的,是干净到骨子里的。我认为这是他探求语言最本真也是最基本的意思,一首诗会在不同时代具有文本意义。如《黎明漫步》:“黎明中诸物,轮廓逐渐/清晰,由多维减至一维/我走在街道一侧的香樟树下/觉察到内心中受伤的某种东西/一种有轮毂、有轮辐的东西/香樟树正在结果。是紫色的/小颗的。我必须重新学习/如何去爱,并且想清楚爱是什么”,平实的话语叙述中,也有小的跳跃和斜刺,读了这首诗后,我会重新定义黎明光亮的内涵,以及散步的意义,以及我在早晨的世界可能的纠缠和困顿。全诗有一种弥漫开来,向四下无限推开去的感觉——所以,余怒这么短的诗,不可能全面解读或剖析事物,也做不到将事物的光影和气韵写足,而只能写瞬间产生的最深切的感觉,本诗中,让我心头一颤的,是:“我必须重新学习/如何去爱”这一句,这一句在全诗不止是意境“升华”之效,还有“四两拨千斤”之作用,正是这么“不经意”的表达,才更有力量。同样,《咏物》这首诗,一段“浪漫的”书写:“从书中我得知/罗马人在鸽子的身上/洒上从花中提取的香水/借助它的盘旋,使空气充满芬芳”,其“浪漫性”也非诗人刻意为之的,而是不经意间成的,我们仿佛看见诗人憨厚的险,为他对读者产生的“惊心”而不好意思。《杂感》是一首极短诗,短短几句话,就道尽人间规律和世间逻辑:“生命徒有其名/如花叶之绚丽/红和绿都必须/附着于一个物体”,从这首诗,仍可看出:即便如生命和人生这样的题材,从相互关系上入手,可以举重若轻。
传统诗歌的优劣,总是以击打人心的力量来衡量的,但我认为,余怒的诗歌依然能够产生读者的阅读感动。尤其是个人的生活阅历和经验恰好与余怒诗歌当中的某一个点相契合,产生的一种微妙的同频共振,哪怕只是一下子或者一小会儿,就能带来回味无穷。这肯定不是同一理念下的某种感召,或者煽动,煽情的东西都是短暂的,只能带来短暂的崩溃式的感动,而不是深入的持久的撼动。我尝试用了一个词叫“钝感”来形容他击打你的感觉,不是让你流血,也不让你流泪,而是有一点点酸楚的感觉,让你想哭,但又想笑。在现实和魔幻之间、浪漫的元素甚至快感也加入了进来。最终形成的感觉也可以说是一种微妙和美好,余怒的诗歌常常会给人带来这样的感觉。正因为他不是对广大诗歌阅读者在追求最广泛点赞量上的订制品,而是我行我素式的根据自己的情感和经验来写作,他的全部诗歌中,可能仅有少量部分能够完全打动某些人,也就不足为奇了。我相信余怒的追求,恰恰是那少量的几个完全被他感动的人,而不是广泛性的强烈但平庸的响应。一个可悲的事实是,普通而平庸的读者群居多,甚至能够独立静心读一首诗的人都不多。现在已进入快餐时代,同时也进入了某种程式的时代,并不鼓励个性思考和独自享用,那种全场起立鼓掌和全剧场嚎哭的场面,实在不是对待诗歌的好态度。读余怒的诗,读一遍是不够的,因为不可能读“透”;更为迷人的,是我读了十遍时,如读了十首他的诗,每一次与我当时的心境有关,与我那一天与不同事物建立的关系有关。同样一首诗,对余怒来讲,不是在原先阅读上的更迭与进一步,有可能是颠覆,获取的是全新体验——这应是诗人所乐见的。
附:余怒组诗《所获》
◎咏物
从书中我得知,
罗马人在鸽子的身上
洒上从花中提取的香水,
借助它的盘旋,使空气充满芬芳。
他们还在马的身上这么做。
马的激情,使芬芳四射,更为浓烈。
但没有东西可以帮助我:
芬芳、爽身粉、思考、行动。
清晨的光线明亮,但我的身上
没有任何东西醒来——或者乐意。
◎反而完美
极端些反而完美。年轻时的心愿:
“把世界献给谁谁”,做她的信仰者。
活在真实中还是虚幻中,
身在世间还是冥界,都不是问题。
五十岁之后,安于老去,
把老年之爱看作人生的巧合,
安于世界的形式和法则所带来的伤害,
持有一切安于现状的正确想法。
◎黎明漫步
黎明中诸物,轮廓逐渐
清晰,由多维减至一维。
我走在街道一侧的香樟树下,
觉察到内心中受伤的某种东西,
一种有轮毂、有轮辐的东西。
香樟树正在结果。是紫色的,
小颗的。我必须重新学习
如何去爱,并且想清楚爱是什么。
◎物与诗
让一个女人回到二十岁,她当然愿意;
让一个破产的人回到他的别墅,他当然愿意。
如今,我可以拿来交换的东西已经不多了,
我有一部出版的诗集,还有一部未出版的诗集。
我老了,证明自己拥有什么变得无关紧要,
愿不愿意交换,取决于将哪种人视为同类。
世俗的欢愉,人间的美景,这一物
与那一物,不过是这一首诗与那一首诗。
◎感性事物
九月的树木干枯挺拔,夜晚
也似是木质的。我躺在河边草地上,
等着那一阵酒劲过去。
一只苍鹭,抓着桥栏杆,
拍着翅膀,做出欲飞状。
这是我今晚看到的第一个感性事物。
一个男人,被他的狗拖拽着,
围绕我转一圈之后离去。
这行为,也充满感性。
冰凉夜空中,有几颗小星星,
俨然诗的结构(比如,三五个词语
组成的短诗句),也充满感性。
◎欲念残骸
昏暗总是宁静的:空中何物之残骸?
或某人梦游之留影。如同我们的构成,
我们的物理存在。被困在这儿。
自我缠绕。完全的占有。彼此倾诉
只是在彼此求证。欲念处于亚语言状态。
◎闪烁
用手电筒捕捉萤火虫的轨迹,
看到夜幕上闪烁的点点光斑。
这里每个人过得都很辛苦,都很渺小。
为满足口娱身娱,绝望于日夜忙碌。
我写诗。甘于渺小。微弱地闪烁。
通过文学去了解一个人,将会一无所见。
萤火虫是通过什么感知我们的?
有一个空中视角,有一个我们所没有的发光器官。
◎宛如
冰天雪地间,我看见
企鹅在列队前行。
打头的是一只步态沉稳的老企鹅,
后面是一群趔趔趄趄的小企鹅。
宛如一颗保守的心,
领着一个有意向的身体——
从“我想”,到“我出现”。
◎这个世界的情诗(四)
世界本身的问候是温和的。
我不预设前提,也不追问结果。无论我
爱过什么,肯定过什么,都是诗人式的。
与世间何物建立亲密关系是重要的。
诗的关系:风景与植物——亦可这么
标示你我。河边有栗树,栗树上有栗子。
◎唤醒方式,或透视法
一幅画那么大的房子、你的悲伤、一只啄木鸟。
很多鸣叫、拍翅声,不仅来自
啄木鸟,也来自
逝去的日子:
它画下的这幅画和你,
它筑造的房子和悲伤。
◎有物如此
把所有正开的、
你触摸过的花都放到床上。
海棠、雏菊、大丽花、紫罗兰。
仅仅是一些芬芳,
单纯的花的目录而已。
在塞满物体的世界上,
有物如此,清澈通透。
我知道你能承受
过多的花蜜,并被它们
点燃;你是有翅膀的,
与肢体的关联并不大。
(原载于《诗潮》杂志2025年3期)


余怒,当代诗人,生于1966年。出版诗集《守夜人》《余怒短诗选》《主与客》《蜗牛》《枝叶·繁花》,著有诗论集《诗的混沌和言语化》《诗和反诗:答张后问》等。先后获第三届或者诗歌奖、第二届明天·额尔古纳诗歌奖、第五届《红岩》文学奖·中国诗歌奖、2015年度《十月》诗歌奖、漓江出版社第一届年选文学奖、2017中国年度诗歌特别推荐奖、第四届袁可嘉诗歌奖、2018-2020年度《安徽文学》诗歌奖等奖项。


陈啊妮,中国化工作协会员,陕西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作品在《诗刊》《诗潮》《星星》《扬子江》《诗选刊》《诗歌月刊》《诗林》《延河》等百余家期刊发表并入选多部选本。评论入围第六届《诗探索》中国诗歌发现奖。著有《与亲书》(合集)。居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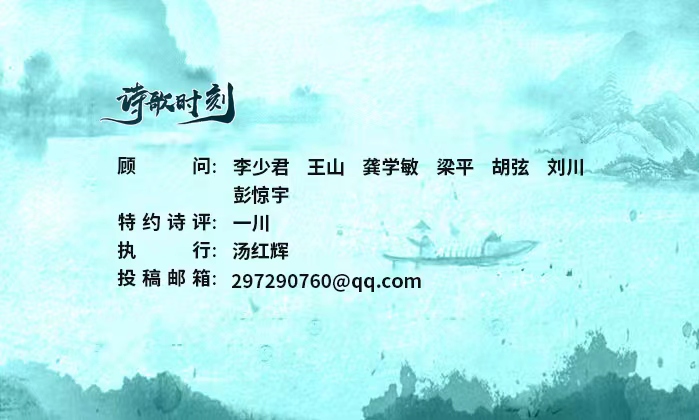
来源:红网
作者:陈啊妮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旅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