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走”的困局与溃败
——姜贻斌中篇小说《最后的铜像》读后
文/贺秋菊
姜贻斌的中篇小说新作《最后的铜像》(《长城》2025年第2期)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省城小巷为切片,通过杂志记者张才华与江湖客刘光头的命运共振,揭开了转型期“出走者”的现实困局、文化撕裂和精神溃败。
一
姜贻斌近年的小说主人公大多在“出走”或逃离,从小乡村、小县城,去往省城大都市。小说集《你会不会出事》(北岳文艺出版社)收录的六个中篇小说中,《我们是亲戚》开篇就写“湘子说要到城里找事做”,他从邵阳乡下进省城长沙的时候“左手提着装衣物的蛇皮袋,右手提着布袋子,布袋子里装了十斤花生”。《我在城里的抵抗》在“我”在老婆的喋喋不休下,想到了“到城里碰碰运气”,于是进了省城。《雪白的月亮》主人公林立去了省城发展,成了“村里最后一个外出打工的中年人”。《跟老鼠说声拜拜》里不相信小县城的工厂会关门、不愿意去省城打工的董子最后也不得不去长沙买毯子。《你会不会出事》的主人公胡丁之从小城先去了海南,后回到省城长沙发展。他们都在以各种方式“出走”小县城。在他们看来,“出走”才是出路,事实上又成了无法逃离的“困局”。
《最后的铜像》里,“有幸调入省城”的杂志社记者张才华“永远跳出了那个偏远的小县城”。在家乡替村里人打抱不平被通缉的刘露明(刘光头)为躲避追捕逃到了省城。两个被命运放逐的异乡人,同在省城人员混杂的底层社区租房相遇,各自携带的不仅是行囊,更是小城基因里根深蒂固的文化密码。省城那条“百十米长的小巷”成为一面棱镜,折射出“出走”者的生存困境。
张才华的“出走”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突围。当他带着木匠的茧手踏入省城编辑部时,那个他一心想要逃离的小县城赋予他的不仅有基层工厂油污,也有对文字救赎的原始信仰。在《生活》杂志撰写奇人异事时,他始终保持着小县城知识分子的道德洁癖。他渴望用文字叩开省城美好生活的新世界,又警惕着江湖故事的虚妄性。他内心的这种矛盾在刘光头表演魔术的现场达到顶峰。当空酒杯凭空被注满酒液时,他既惊叹魔术的魔幻,又焦虑报道的真实性,恰似小县城文化对都市奇观的应激反应。
刘光头的逃亡则是乡土规则的暴力外延。这个在小乡村以拳脚建立威权的江湖客,因身怀硬功夫和魔术绝技,逃亡省城在一次打架事件后被正在寻找传奇故事的记者张才华找到。报道发出后,杂志、记者张才华都成了受益者,而刘光头本人更是成为江湖传奇人物。他组建公司,行走江湖,日子过的红火,并收留了众多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亲友,将宗族社会的生存法完整地移植到省城。他收容乡亲时表现出的家长式庇护,处理公司纠纷时采用的乡约调解,最终没能逃出“出走”的困局,不明不白地中毒身亡。这一切都印证着小县城的乡土伦理在都市语境中的水土不服。那间“地板上摆着一对哑铃,半空中吊着肥肠样的沙袋,木椅上摆放着几本发黄的旧书”的出租屋,成为他调和乡土侠义与都市规则的中转站,却终究未能完成文化基因的突变和人物身份的重构。
二
社会转型时期,每个人都在进行着残酷的身份实验,在金钱与道义的拉锯战中,现实的失败恰恰应证着精神的溃败。
与张才华和刘光头的“出走”不同,刘小英是省城人,在印刷厂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只是父母没有工作,需要刘小英补贴家用。她与张才华的爱情始于白纸裱糊的素朴理想,终结于五粮液的刺目金光。当印刷厂的工资无法填补原生家庭的贫困沟壑时,刘光头公司的财务权杖成为她唯一的救命稻草。她收集刘光头报道为“出走”做准备,匕首首先刺死纯真的爱情。她的“出走”本质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底层突围,金饰加身的背后,是无数个深夜对账本时滴在数字上的眼泪。从拒绝当“托”到默许公司账目造假,从羞于谈钱到主动询问“分成”,刘小英的道德底线随着存款数字攀升而不断下沉。她的转变并非简单的物质沉沦,而是在生存压力下完成的底层突围。当她戴着金饰重返省城时,首饰的耀眼光芒恰似小人物在时代裂变中灼伤的疤痕。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并未将刘小英的转变简化符号化,而是通过她偷偷保留刘光头铜像,在电话里流露对张才华的眷恋等瞬间的柔软采撷到资本异化尚未完全吞噬的人性微光。同样作为“出走”者,她身上携带着挥之不去的小县城文化胎记,她接济父母、供养妹妹,这些都是乡土伦理的延续。当然,另一方面,她又用签订劳务合同这种最现代的契约精神来践行道德义务,甚至最后要以市中心买大房子来诱惑张才华。
张才华的妥协显露的是一代“出走”知识分子的精神溃败。他们最初拒绝当“托”,有着强烈的道德焦虑,在日复一日的消耗中,开始默许杂志打擦边球操作,又接受了主编安排的现实婚姻,他的每次退让都在消解小县城赋予他们的理想主义。那个在省城湘江边疯狂寻找未婚妻的小县城青年,最终成为在这套现实体制黄昏中等待解散的中年。这种身份褪变恰恰印证着转型期知识分子的集体彷徨。当刘光头的铜像隐入市井、杂志社解散、人员面临重新安排,废墟上作者或在诘问,在狂飙突进的城市化进程中,那些带着小县城记忆的出走者,究竟是被新时代接纳的移民,还是永远流浪的文化弃儿?答案或许就藏在小巷深处那盏昏黄的孤灯里。
杂志社与刘光头的江湖公司构成转型期的命运共振。《生活》杂志靠猎奇故事维系着五十多万份发行量的辉煌业绩,刘光头靠世间罕见的硬功夫闯荡江湖获得盛名,二者本质上都是消费主义初潮催生的文化奇观。当“木匠”记者张才华在“铁匠”主编的授意下将刘光头包装成“奇人”时,文字与拳脚共同沦为商品符号。这种共谋关系在杂志停刊与公司破产时轰然瓦解,暴露出转型期文化生产的速朽本质。
三
当刘光头的铜像从宝庆饭店门前消失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江湖传奇的陨落,更是一个时代精神基座的震颤。姜贻斌用手术刀般的笔触,在省城陋巷与江湖风云的接缝处,为我们保留了历史的横截面,剖开最隐秘的病灶。
张才华的钢笔与刘光头的拳套,在省城出租屋里形成的奇妙共生关系,恰恰印证着这种文化迁徙的阵痛。当县城木匠成为都市记者,当乡村武夫变身江湖明星,他们的身份转换始终带着原乡的烙印。张才华报道奇人异事时下意识的道德犹疑,刘光头管理公司时惯用的宗族思维,都是小县城文明植入的精神胎记。这种文化基因的顽固性,在刘光头坚持不用“大师”称号的细节中尤为刺目——与其说是江湖道义的坚守,不如说是小县城伦理对都市规则的悲壮抵抗。那条藏污纳垢的百十米陋巷,俨然成为转型期的文化飞地。在这里,木匠的刨花与武夫的汗臭奇妙交融,知识分子的启蒙叙事与江湖客的生存哲学激烈碰撞。当张才华为是否加入江湖公司辗转难眠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人选择困境,更是两种文明形态在个体精神空间的惨烈厮杀。
“最后的铜像”从饭店门前消失的瞬间,铭刻着乡土伦理、江湖道义与宗族纽带的正在集体性消亡,宣告着一个依靠肉身技艺与道德信义生存的时代的终结。然后,铜像终未被彻底销毁,而是被刘小英秘密收藏,暗示江湖侠义虽被时代放逐,却仍在民间记忆的褶皱中倔强留存。当我们在小说结尾处回望这座蒙尘的铜像时,看到的不仅是奇人刘光头的执念,还有那些被时代放逐的“不合时宜者”的张才华、刘小英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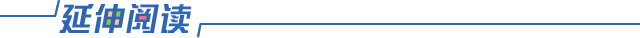
留下的不仅仅是铜像(创作谈)
文/姜贻斌
小说中的人物有点生活中的影子。
某天,我突然想起了这个人。
其实,当年我跟他的交道并不多,仔细想来,总共见过两次面吧。无非是当时他来我们杂志社表演节目时,我帮过他而已,比如拿道具(扑克、图钉、黑板),以及搬桌子等等,却绝不是他请的托。这一点,我可以对天发誓。只不过,这个人的确很神,不知是玩魔术,还是运用其他什么手段,竟然把几个节目玩得出神入化,精彩绝伦,让我们大开眼界,放肆鼓掌。他是因为我当年所在的那个杂志发表的一篇人物特写,而名声大噪的,一时传得神乎其神。为他写东西的是另外一个记者。
后来,我们当然就很少接触了,几乎没有了什么来往,只是听说他在省城搞得风生水起,他表演的节目,也很受人们欢迎。他摆在饭店前面的那尊铜像,我是见过的,而这种做法是比较罕见的,我估计省城他是唯一摆着自己铜像的,它就摆在离我们杂志社不远的中山路上,我间常经过那里,却从未进去过。当然,关于他的点点滴滴,还是时有耳闻。听说他心肠很软,甚至把乡下的七大姑八大姨,三舅五叔,全部搞到省城的公司,一起“吃”他这个大户。因为他疏于管理,难免不人浮于事,不明争暗斗,不挑拨离间,不惹是生非,这弄得他很是烦躁,心力交瘁。这也够难为他的了,既要操心众人的生计,自己又要练功表演。哪怕有八个这样的老板,公司也会毁掉一旦,前功尽弃。
我先是想写写这个有点武功、玩点魔术的男人,是如何在社会上生存的,它应该是幽默的、调侃的,同时写出他的灵活和狡黠。写着写着,思路居然就有点海阔天空了。心想,可以挖掘他在开办这个公司时,虽然心肠良善,养活了很多人,但因为管理无序,任之听之,最终不了了之。因此,他同他的公司一样,终究会被时代所淘汰。
是的,留下的不仅仅是铜像,它还有让我们有更多的思考。
谢谢《长城》,谢谢责编雅丽女士。

姜贻斌,湖南邵阳人。著有长篇小说《左邻右舍》《火鲤鱼》《酒歌》,小说集《窑祭》《孤独的灯光》《漂泊者》等多种。
来源:红网
作者:贺秋菊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旅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