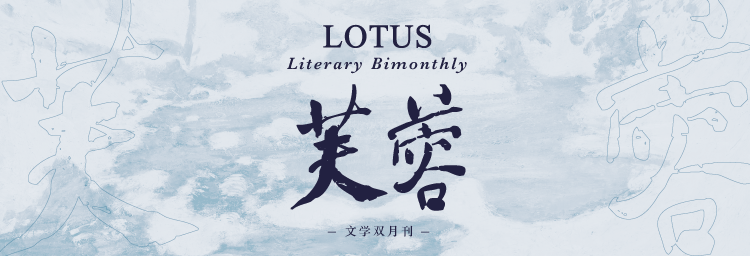

客厅亮着一盏灯
文/古年
儿子回来了。
不急不慢地朝这边走过来,远远看见一张苍白的脸。如果不是他身后拖着一个贴满行李条纹码的绿色行李箱,光看穿着,还以为他只是去附近的超市转悠了一圈回家的。
母亲逸枝心头一紧,抓住丈夫的手要一起迎上去,却感觉对方的手在拼命把她往后拽,身体瑟瑟发抖,脸上的皱纹里蓄积了恐惧。
儿子走到距离两位老人还有五米的地方停下来了,取下口罩,说:“妈,爸,我回来了。”声音有些干涩,他又补充一句,“来陪你俩了。”
逸枝抖动了半天嘴唇,说:“你总算回来了。我们都以为这辈子见不到你了。”
儿子的发型与十年前离开家时相比没有改变。一撮前发遮住了右眼,露出的另一只好像被刺眼的光束照射着似的,总是有些躲闪。
逸枝的眼眶还是让这目光烫红了,叹了口气:“你瞧瞧我俩,都担心你认不出来了呢。”
被她紧紧拽住的丈夫把脸扭到一旁,完全无视儿子的存在。他冲着身后的一个女子抬起正哆嗦的脚大声抱怨:“为什么不给我穿袜子?到了夏天怎么还不穿袜子呢?”
那女人却顾不上搭理他,迎着五米外的男人走去,微微鞠躬,赶紧接过对方手中的行李箱拉杆。
“快,快先进屋吧。”逸枝这才回过神来,侧身给儿子让路。儿子点头,一只眼睛开始向四周张望。这是东京郊外一幢老式两层独栋住宅,屋顶的蓝色瓷瓦已经被雨水冲洗得泛白,庭院小径的几块飞石也被鞋底磨得像河床里的卵石般铮亮。只有院子四周灌木树做成的藩篱修剪得齐齐整整,像是刚从理发店走出来推了一色的平头。
黑岩泽在三人簇拥下走进了玄关,刚要脱鞋,父亲居然抢先趴在他脚下了,伸手帮他解鞋带。刚才脸上的惶恐变成了讨好的涎笑。他也不拒绝,等鞋脱下来后几乎是从父亲的秃顶上跨进了客厅。
他打量了一下室内的四周,眼里露出来的是打开酒店房门的表情。一家人却慌乱起来,让座的,整理沙发靠背的,拉开窗帘的,加上父亲硬要帮他把脱下的外衣挂到客厅里根本不存在的衣架上去。
“要不是这场疫情,恐怕死了也见不到你了。”妈妈又在低声嘟囔。她的眼睛始终没离开过儿子的脸。儿子那张白瓷般的娃娃脸未变,只是嘴唇上下多了剃须刀刮过后留下的青黑,没被前发遮住的那只眼睛放出幽亮的光来。
儿子避开妈妈的眼光,说:“这和疫情有何干系,我不是三个月前就说要回来的吗?”
母亲并不听解释,抖着手要摸儿子的脸,又胆怯地缩了回去,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说:“这不是做梦吧?我怎么一点没有儿子就在身边的感觉呢?”
这时,端着茶具的女子走过来,沏好放在沙发前茶几上。正要退下,被逸枝一把抓住了手:“都忘记介绍人了。泽君,这位就是一直在家照顾我俩的护理小姐。”
“我是一辽瞳子,请多多关照。”
瞳子俯身抬起头时,露出一张微胖的脸。眼睛里面蓄满了女性的温柔,笑起来一排洁白的牙齿和嘴角边一对浅浅的酒窝有些抢眼。
他点头回礼,只在等待对方抬头对视的那一瞬间,眼里有了一抹异样的神情。
“不许乱说!你连自己名字都记不住吗?真纪子。”一旁的父亲突然亢奋起来,对护理小姐眼睛一瞪。
“死老头呀,你儿子回来了也不认识吗?他是真纪子的哥哥,您的儿子泽君啊。”母亲冲着丈夫黑岩隆雄嗔怨,又转身望儿子,露出歉意的笑。
父亲却不依不饶:“为什么你们知道他是我儿子呢?”
母亲一愣,说:“泽君,别计较,你爸几年前就这样了。他现在连我是谁都不认识了。”
黑岩泽摇摇头,说没事,又冷言道:“不过,他要是一直都这么痴呆,一家人也不至于这么惨,只剩你俩形影相吊。”
瞳子赶紧岔开了话题,说:“黑岩泽先生,您母亲想您回来都快急疯了呢。她把您从中国打来的那个电话录音听了不下十遍,每次都问,这不是骗人的电话吧?直到您从机场打来电话说正在等待核酸检测结果时,才终于相信了。”
母亲有些不好意思,说:“这也不能怪妈。NHK播放的电视节目总要老人提防诈骗,加上疫情来了,诈骗的人也活得用力了吧,时不时就来电话。不过,有人陪着说说话也行。”
瞳子点头:“我把黑岩泽先生刚从中国汇来一笔护理费的事告诉了大妈,她才相信您真是出国了。听说您住在深圳,又托我去东京神保町一家书店买张中国地图来看呢。”
逸枝说:“其实瞳子把手机上的地图给我看了,可那么小的屏幕怎么也看不明白你离家有多远。”
黑岩泽听了没变表情,说:“您就这样不相信自己的亲生儿子吗?”
“都十多年没你的音信,我该怎么相信啊。”
一旁的父亲马上插话:“我该怎么相信啊。”
黑岩泽看来没兴趣继续这个话题,他端着茶杯,跟在瞳子身后走进了厨房。见瞳子打开冰箱要取什么,突然走上去,从背后捏了一把她翘起的肥臀。
对方吓了一跳,立起身子时差点脑袋撞到了冰箱门。她很快镇静下来,抓住那只手,用刚取出的黄瓜敲了下对方手心:“去去去,你在父母面前表演一下这德行。”
这时,客厅里传来了嘈杂的人声。是街坊邻居来看两老的儿子。听声音便知道,都是父母的同辈人,也只有他们会对一个消失了十多年的孩子保持好奇心。黑岩泽有些心烦,赶紧从厨房通向院子的侧门溜了出去。他猫腰穿过客厅正对庭院的窗户,走到唯一的大树底下,坐下来,仰头看树上结满的柿子。刚刚立秋,柿子的表面涂上了一层隐隐约约的白霜。
不知什么时候,母亲站在他身后了。本是要叫他进屋去问候街坊们,却一下被儿子的表情阻止了快到嘴边的话。
“是不是记起来了,你常爬到这树上去跟姐姐摘柿子的光景?”她问。
黑岩泽起身,摸着树干上一个发黑的疤痕,说:“我只记得这根做脚架的树杈是怎样被父亲砍掉的。”
逸枝无语。她当然也没忘,小时候儿子被父亲追着打,他就一下蹿上树去不肯下来。有一天,又要猴儿似的上树时,发现那根做脚架的树杈没了,被追上来的父亲用脱下的鞋底抽打得屁股红肿,好几日走路跟孕妇一样。
“后来你常常躲进地下酒窖,把门给堵死,你爸拿你没法子。”母亲想为回忆加点光亮。
不料儿子突然盯住母亲,问:“我很好奇每次被父亲追打时,您到哪儿去了呢?”
逸枝赶紧避开儿子的眼睛,用手捂住了脸。
(节选自2024年第4期《芙蓉》【海外华语作家小说专辑】古年的《客厅亮着一盏灯》)

古年,旅居日本30余年。社会心理学硕士,经营管理培训师。自1998年开始在日本各知名跨国企业从事跨文化经营管理培训至今。曾在《收获》《作品》《延河》《湖南文学》《香港文学》等刊物发表多篇中短篇小说、散文。出版作品包括《中国经营顾问传授跨文化管理技法》《中国式谈判》等日文著作。另在日本数家刊物开设专栏,发表多种主题的散文随笔。
来源:《芙蓉》
作者:古年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